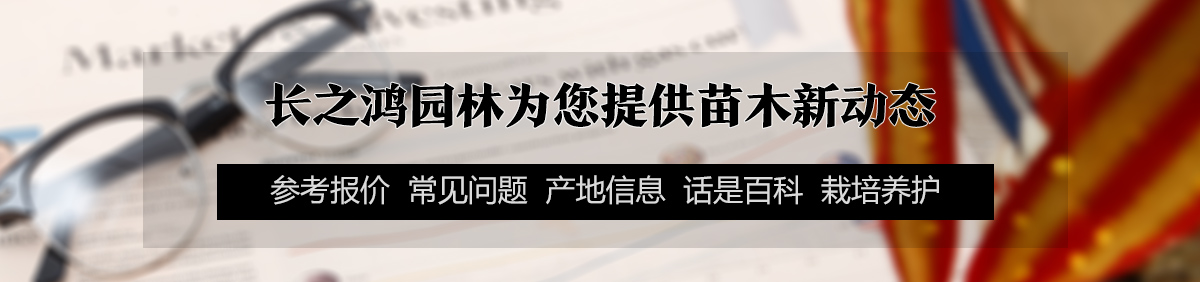听他们讲述西柏坡的故事(史进平)
曾彦修是我们拜访的第一位老人。他精神矍铄,记忆力好得惊人,50多年前的事儿,就像发生在昨天。他的身份是西柏坡时期新华社总编室评论组成员。
曾彦修:我是1948年11月被调到西柏坡中央大院新华社小编辑部的。到西柏坡后,亲身体会到了很看重抓“文武两杆子”,文的是宣传部门,武的是军委作战部门。正常的情况下,除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必须在他身边,其他中央部门可以离中央远一点,但中央宣传部门和军委作战部门必须跟在他身边。文的方面,因当时中宣部人很少,宣传报道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新华社和中央政策研究室来做。
新华社总编室在同志住的大院的前院,共走一个大门。前院为三间小平房(约40平方米),东边一间是和谷羽夫妇的办公室兼卧室;西边一间是陈克寒、吴冷西办公的地方;中间一间较大,房屋中央由三四张长条桌拼起来,两边各坐四人办公,这八人是朱穆之、方实、黄操良、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我和王宗一。朱穆之、方实是军事组的,因为他们每天发的稿子最多,时间性也强,为了工作方便,就坐在紧靠住处的地方。紧挨着方实坐的是国际组的黄操良,当时国际组就他一个人在西柏坡,其他人在总社,他的稿量不是很多,但涉及外交,政策性强,所以也靠住处。其他五个人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我和王宗一是评论组的,由于重头文章等同志亲自动手写了,评论组自己写的东西不多,所以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些。陈克寒、吴冷西那时最忙,每天除了埋头看稿子,还要管业务行政。当时军事报道稿子多,朱穆之那时也特别忙。城市组、农村组的同志们则在前院两厢房办公。
曾彦修:1948年秋,我在东柏坡中央宣传部工作,中央把撤离延安时藏在陕北的书籍运到了东柏坡,散放在一间屋子的地上。见此情况,我便与共事的于光远同志商量,应该做一些箱子把这些书放起来,再转移时也方便些,还利于保存。随后,我们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汇报了这个想法,当即决定请夹峪村的木匠用榆木做四五十个结实的大箱子。当时每个箱子花费边区币约4元钱。书装进箱子没几天,就传来了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消息,要紧急转移。于是在一个夜晚,东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排成一字长蛇,从9点干到12点,手递手地把箱子传到在东柏坡村口的一个窑洞里,并用枯枝和树叶隐蔽起来。后来虽然偷袭没成,大家依旧是觉得我们想的这个主意好。进北京时这些箱子也派上了大用场。
余宗彦是西柏坡时期新华社总编室解放区组组长。在去余老家之前,我们得知他由于上了年纪,听力和表达能力都不是很好。见到余老时,他在女儿余灵灵的陪护下,由她女儿代我们与余老进行了文字交流。在经余老同意后,余灵灵拿出父亲十年前自己整理的一本稿件集,其中有余老的回忆文章:
1948年8月,我到距中央所在地不远的李家沟,不久调到西柏坡新华社,先后担任编辑、副组长、组长。
在余老的抽屉深处,还存有一件珍贵的文物——余老自己在晋绥搞土改时写的有一万多字的《山西甘泉村土改调查报告》。报告内容丰富,调查数字有理有据。老人如此认真地收藏它,它一定饱含了老人不少的心血,记载着老人年轻时对革命的无限热情。也正是通过这件珍贵文物的详细记载,我们得知余老是在参加土改结束后被调到西柏坡中央旧址大院的。
在合影留念时,我发现老人有些激动。他使劲拉着我的手,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
计惜英是西柏坡时期新华社总编室解放区组工作人员。计老身体很好,腰板直直的,记忆力也不错,只是听力不大好,听话需要借助传话筒(即一个特制的硬纸筒)。
计惜英:1948年秋,参加土改工作结束后,廖鲁言说你不要到别处去,到我这里来工作吧!就这样,我在陈家峪新华总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了西柏坡中央旧址小编辑部。
计老风趣地谈起当年到洪子店用每月两元钱的“工资”去买酒喝及在南庄搞土改的事情,说当时虽然生活很艰苦,但革命热情却很高涨,工作生活丰富而充实。
计惜英: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前线将领们纷纷来到西柏坡,大家脸上都带着胜利的喜悦。当时编辑们在一起说笑:东北高岗最神气,穿呢子大衣,抽50支铁筒555牌香烟;华东陈毅也好一些,穿蚕丝衣服;只有西北彭老总最艰苦,穿解放区的粗布衣服。有一天,我正在门口站着,见主席由东面过来,一边走一边喊:陈毅!陈毅!原来陈老总当时住在西柏坡新华社总编室旁边的军委作战室厢房里。没一会儿,我在厕所碰到了“大胖子”陈毅,陈毅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上海的,他兴奋地问我:“我们马上要解放上海了,你想不想回去?”
计老一边说,一边拿出上海解放时自己英姿飒爽的一张照片,说这是在解放上海时入城式的主席台上照的,是唯一的一张。
计惜英:那是三大战役期间,有一次,有个较急的稿件,交给田林,要求他细校后发出去,田林不知怎么回事两天没有处理。知道后,对这种工作不抓紧、拖拖拉拉的工作作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说“腐败,真是腐败!”由此可见,当时的“腐败”与现在的“腐败”含义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次,让当时担任业务秘书的吴冷西校对一份中央,结果吴冷西给遗失了,并且查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这时吴冷西向乔木表示:“实在找不到,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吧!”乔木同志当即严厉地批评说:“不行,这是中央,是一定不可以遗失的,一定要把它找到!在我们这里遗失了,怎么向中央作交代呢?除非内部有坏人。这不是小问题,必须彻底查清,应当相信是可以查清的。”由于乔木的格外的重视和严加督促,经过同志们里里外外地仔细查找,最后终于在柜缝里找到了。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过这次事件,同志们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保密教育,一次对待工作要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的教育。
田林是西柏坡时期新华社总编室唯一的女编辑。我们去的时候田老已等候在大门口。田老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西柏坡》,开头是这样写的:“每个人的生活史上都有难忘的几页。30多年了,只要想起来,平山县西柏坡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对于我都还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亲切!”老人很健谈,说话很干练。
田林:总社到达西柏坡后,党中央恢复并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不仅审阅所有要发表的稿件,而且还通看新华社各地方分社和野战军分社的所有来稿(这些来稿除时间性强的随到随编随发外,其余的都排印出来)。
每天晚上9点左右,在大家完成了一天的编写任务、乔木同志也审完所有稿件之后,他照例召开编辑会议(当时戏称“记者招待会”),主要是由他谈对当天稿件的意见。这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会议。会上乔木同志传达毛主席、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的指示,评点稿件,大家各抒己见,议论风生。乔木同志对稿件的意见,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从稿子的主题思想、体现的方针政策及至文字技巧、错别字等等,都要求特别严格,评点入微。修改之后,还经常把写稿的同志找来,讲明为何需要这样修改,提醒写稿的同志以后要注意的事项。大家在会上可以解释、辩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乔木同志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大家不能不口服心服。有的稿件被他从头到尾批得体无完肤,要求重新撰写,有的稿件经过三次、四次返工才获通过。像范长江这样经验比较丰富、全国闻名的老记者,他写的一篇战局评论也受到过乔木的严厉批评。事后范长江对吴冷西说,若不是在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过程中常常看到陆定一同志和同志起草的稿件被毛主席修改得等于重写,很受教育,他根本接受不了乔木的意见,要是在《大公报》,他早撒手不干了。乔木同志折服众人之处,在于他不仅能指出别人的不足,而且还能自己动手写出或改写出的确艺高一筹的佳作。《屠夫、奴才和白痴》就是他重新改写的一篇评论。
刚来西柏坡的同志们对乔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不适应,感到有压力,稿子编写出来后,犹豫再三,不敢送审,怕通不过。但时间一长,同志们便逐渐适应了,都感受到在乔木领导下工作,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方实是西柏坡时期新华社总编室军事组成员。我们到方老家的时候,方老正在做理疗,他从美国回来照顾他的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起父亲的敬业,她说直到去年父亲身体健康情况不允许时,他才从《炎黄春秋》杂志社完全休息下来,80多岁的他一直在做责编,还自己亲自审稿。没一会儿,方老出来了,尽管由于中风走路需要人搀扶,但他脸色红润,气色不错,依然能够准确的看出年轻时的英俊与潇洒。
方实:我被调到西柏坡小编辑部主要是编写战报。开始只有我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又把朱穆之同志调来负责战报的编写工作,我协助工作。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受益很深,像是进了一次短期学习班,从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到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立场,应掌握的党的方针政策,应具备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是一次很有成效的训练。
华北记者团到西柏坡,我们这一批在西柏坡工作的新华社编辑们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亲耳听到了少奇同志的讲线日,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勃率领的记者团来到了西柏坡,少奇同志对新闻工作十分重视,接见了这批记者,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内容丰富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指出报纸的重要性,说:“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摩擦。新闻工作做得不好,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少奇同志的报告足足作了将近3个小时,人们听后都十分满意。大家一致认为少奇同志的报告不仅提高了大家对新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了大家对自身工作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新闻工作者应具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时时不能忘记我们是人民群众的通讯员,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
朱穆之是西柏坡时期新华社总编室军事组组长。我们在新华社接待室见到了朱老,他耳不聋,眼不花,腰板硬朗,说话洪亮,是我们所采访的老同志中身体健康情况最好的。老人脸上总带着笑容,我想这也是老人长寿而健康的原因吧。
因为1991年10月朱老回过西柏坡,并给西柏坡纪念馆题过词:“中国命运定于此村”,话题由此开始。
朱穆之:当时在军事胜利形势下,捷报频传,我军每天都要攻占一些城市,解放大片地区,歼灭大量敌人,因而每天都要发许多战报以及军事通讯和评论文章,工作是极为紧张的。一般的战报,小编辑部可签发,重要的战报,经乔木同志看过后还要送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审定才能播发。很重要的战报,最后需送同志批发。当时很多的战报都是从我手里发出去的。又回到西柏坡时,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所以挥笔给西柏坡题了词。
我印象最深的,是乔木同志对编辑行政负责干部要求很严格,要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写稿、编稿上面,不能只忙于日常编辑行政事务。在一次宣布小编辑部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的会议上,乔木同志着重指出:“过去编辑行政负责干部脱离编辑业务,好的编辑人员被提升为编辑行政领导后,即脱离业务,忙于行政工作,致使编辑工作质量不能提高,这是党的新闻事业中的一个损失。今后必须纠正这个偏向,一切编辑行政负责人必须同时又是强有力的编辑工作者,行政业务要尽可能减少,主要精力应放在写稿、编稿上面,编辑组长、主任及至总编辑都应当这样做。”
朱穆之:在西柏坡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同志审稿首先是从政策和政治上考虑问题:一篇稿件符不符合党的政策,在策略观点上有无问题,有无“左”右倾偏差。在分社来稿和我们编发的稿件中,发生这类错误较多的是有关宽待俘虏的报道,“读者信箱”中有时有反映。解放战争后期,作战胜利慢慢的变多,高级将领大批被我军俘获,宽待俘虏以瓦解敌军的报道在这一段时期的军事新闻中占很大比重。这类新闻经常发生的毛病是过分强调“优待”的一面,因而不断地出现右的偏差。在审阅此类稿件时,都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批评,要求“学习在正确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正确的策略,才不至于犯错误。”
当谈到旧址内办公室布置时,我们拿出时任新华社编辑部评论组成员曾彦修老人画的座位图。朱老看了看,清楚地指出了自己办公的位置——最靠近乔木办公室的地方。
朱穆之:小编辑部四间正房坐北面南,是插嵌房,东侧是乔木与谷羽夫妇的卧室,卧室内有一土炕,炕上放有小办公桌。西侧是范长江、石西民等领导的办公室(与曾彦修的回忆不符,可能某个人的记忆有偏差——编者注)。我们七八个人在中间屋办公,非常拥挤。我常常在阳台上(嵌台儿)坐着木墩子编稿子。关于屋内陈设,就是简陋的桌椅,桌子根本不算得上什么桌子,就是当地人的门板儿加腿,没有抽屉。椅子是农村常见的屋凳、木墩。
不知不觉我们已谈了两个多小时,老人仍然谈兴不减。我惊奇于老人的身体,竟然一点也不显疲惫。当我笑问朱老保养身体的秘诀时,朱老风趣地哈哈大笑说,没什么秘诀,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吧:
朱穆之:我国一个访问团到苏联去访问,途中经过一个高寿村,村里全是90多岁的老人。记者走入一家农户,见着98岁的老爷爷问:“老爷爷,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老爷爷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多运动……”正说着隔壁屋传来一阵大笑声,声音更是洪亮有力。记者问:“这是……”老爷爷说:“这是我哥哥,他喝醉了,天天这样。”
朱穆之讲完后,自己又笑了起来。我们领会了故事的意思后也大笑起来。朱老语重心长地说:“没什么秘诀,心态最重要。”
采访结束后,回想着每一位新华社老人及他们的谈话,自己也感觉融入到了西柏坡那紧张而火热的生活中,心中也充满着火一般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