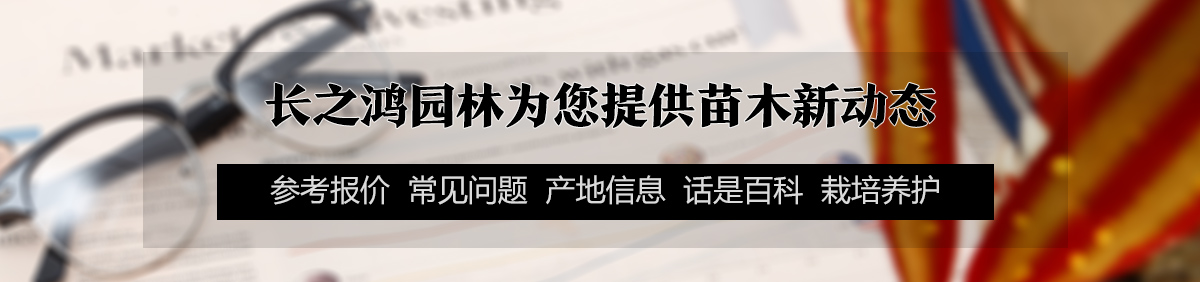浙南往事:玉壶岱头的历史风烟
这是玉壶方言,给在这里念第四声,许配的意思。排粥指白粥或稀饭。这话的意思是生养了女儿,不要许配给东头人,因为那里缺水,稀饭好吃(意指稻谷多)可水难挑。另一句是:养囡灰给东头山,毛露洞(方言,指雾气笼罩)上间,鸡务(方言,鸡粪的意思)满道坦。这句话是说东头海拔高经常被雾气笼罩,村民经济来源少,靠养鸡养鸭换取一些生活用品。

这两句俗语产生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时东头至玉壶没有公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因此玉壶本地一些女子不愿嫁到东头。如今的东头已与从前截然不同:公路到家门口,自来水进了家家户户,村民出国的出国,工作的工作,经商的经商。此地森林覆盖率大,空气清新,在外辛劳半生的人都乐意回归家园养老。安居此地的我们正常的生活安然闲适。

岱头村位于玉壶东北方,由岱头、双丫树(此地一棵大松树有两个大树杈,故名)、方丘等自然村组成,建国时属吕九乡,1952年归东头乡,1955年建初级社时改名岱民村,公社化时称岱民大队,1984年改称岱民行政村,村委会驻地岱头村。

为何称岱头?答:此地在岱根后山,山像袋形,村在袋口,地人称之为“袋头”,后改称“岱头”,为原东头乡政府驻地,设有供销社、乡校、卫生所等单位。
岱头村东连坳头,南接岱根,西靠东丘,北依南林。旧时,从岱头东行至茗垟,南行经岱根到吕溪和玉壶,西行经金星到十源,北行上黄河经宫岭至雅龙和朱寮。这里山岗林立,丛林茂密,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据《文成乡土志》记载:岱头始居者为王氏。王氏是从哪里搬来的?何时搬到这里的?没有答案。村民则告诉我:岱头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在胡氏搬迁到这里之前,前朝人在这里居住,后官府派兵剿灭全村,整个家族就消失了。官府为何要剿灭岱头王氏?岱头?前朝人?王氏?是否就是岱头王?谁也说不出所以然。

继王氏之后搬到岱头的是胡成台和胡荣发。据《胡氏族谱》记载:家住玉壶上村墙围底(蒋氏祠堂边上)的胡大江之孙胡成台为玉壶胡氏第廿六世孙。胡大江之弟胡大涧之曾孙胡荣发与胡成台关系甚好。胡成台和胡荣发为堂叔侄,两人时常一起去种田割草。族谱上没有胡成台与胡荣发的出生年月,但记载了胡成台之堂兄弟胡成寰生于明万历壬寅年(1602),我们只可以以此推算出胡成台的大致诞辰。
胡成台和胡荣发为何要搬到岱头?与一场“瘟疫”有关。有一年夏秋之交,玉壶爆发一场大面积的“瘟疫”(玉壶人称瘟疫为黄塘姑瘟)——痢疾。鉴于当时的经济和医疗条件,这无疑是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疾病。“黄塘姑瘟雷(玉壶方言,盛行的意思)起来啦。”惊恐不安的人们不敢外出,不敢与他人接触。街坊邻居时常听闻谁得了痢疾,高热惊厥,甚则昏迷而导致死亡。一时间人人自危,玉壶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玉壶本地人多,痢疾传染快,如果远离人群就能避免被感染,走,到深山里,离群索居才不会被感染。
一天早上,胡成台和胡荣发每人腰间捆上一把刀鞘,又顺手拿过一把柴刀插在刀鞘上,走过栋头棋盘,跨过芝溪,沿着旁山路往前走。叔侄俩沿着芝溪畔一路向前,前方没有路,乔木和灌木混生,杂草有一人多高,人根本就过不去,怎么办?砍,手起刀落,一株株灌木躺在柴刀下,他们得以前行。他们终于走到岱根,抬起头向东北方望去。“你看,那座袋型的大山丛林茂密,我们要是居住在那里,什么黄塘姑瘟都到不了。”那就去吧。可怎么样才可以到达那里呢?沿着山脚往上爬。两人过岱下,沿着马龙岗继续前行,快到山顶时,只见一处山坳背风,阳光充足。胡成台兴奋得一跺脚,“我们住在这里。”说做就做,他们砍树割草,垒石筑墙,搭起草屋得以安居。这里没有地名,因为住的是草屋,故名草屋基。
夜晚的草屋基,浸在秋虫的呢喃里,浸在山风的私语中。胡成台和胡荣发躺在草屋里,看着黝黑的夜幕上繁星点点,听着草丛里虫声四起。“切切暗窗下,喓喓深草里。”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漫长的深夜里,只有凄切的虫声走进叔侄俩的耳鼓,成为他们最能表达孤独心情的象征。是呀,为了活下去,离开亲人和朋友,何以为伴?唯有秋虫,唯有这片山野。
胡成台和胡荣发开荒地种番薯种洋芋种菜,又在草屋边上筑田坎开了两块田,引水种水稻。因为勤劳肯干,两人积累了一点钱财,该成家了。其后,胡成台娶妻周氏,育有一子胡荣顺。胡荣发娶妻吴坑坳林氏,育有一子胡延元。悠然的炊烟,清脆的童音,碧绿的稻田,清晨的鸡鸣,傍晚的狗吠,这片原本荒凉寂静的山林从此充满勃勃生机。

草屋在山坳里,这里坡度大,不宜聚居。随着家族成员的持续不断的增加,胡氏后裔逐渐向上搬迁至仰口坦和屋基底,其后又不断向四周延伸,于是有了大份老屋、第二份老屋、第三份老屋、第四份老屋、株垄老屋、屋基底老屋和双丫树老屋等。

寒暑几度春秋,岱头依旧祥和。胡氏就这样在岱头生根发芽,瓜瓞绵绵,营造出一个安宁和谐的聚集村落。
继胡氏之后来到岱头的是周氏。约100年前,金星、吕溪、东头合称为金吕乡,乡长是岱头人胡准(谐音)。胡准是地主,家境富裕,田地多,且为人大方,对兄弟姐妹极为关心疼爱。胡准的姐姐嫁到玉壶山背周家。诞下二子后,其姐夫不幸英年早逝。两个幼子一个寡母,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为了更好地照顾姐姐和外甥,胡准让姐姐带着孩子来到岱头,住在株垄。就这样,周氏在岱头繁衍生息。
我们接着来说赵氏。20世纪40年代初,家住大峃西山岩头的赵沛横育有四子,因家里人多地少,老二赵东斋、老三赵东仙和老四赵东再决定外出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家里的田地留给老大。兄弟三人沿着大壤岭、项山、半岭、五铺岭来到玉壶,又沿着芝溪逆流而上垟头、潘庄亭、岱根、岱头,在株垄北侧的后寮搭起草屋种山厂。

草屋基在哪里?从屋基底老屋往南走,过地主殿门前,顺着一条山间小路往南行,约50米处有一块大石头,前方杂草丛生,道路已被湮没,我们只得停下脚步。这条路是古道,胡成台和胡荣发从岱根前往玉壶走的就是这条泥路。后来,有人在驮(大)岭以块石和卵石铺设了一条山岭,这条泥路就荒废了。如今因鲜有人走,此路已经堵塞。

我站在大石头上往下望,草屋基在一棵松树前方,被杂草掩盖着,已经看不出模样了。我问:胡成台和胡荣发开辟出来的稻田呢?“就在草屋基边上,就在那里。”我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望去,那儿是一片杂草。

是呀,400多年的光阴,能让多少曾经成为过往?能让多少身影隐入历史?能让多少脚步声化入泥土?当年的草屋已回归山林天地,湮没在历史的云烟深处。那丛林之中,那茅草深处,可还有胡成台和胡荣发那寂寂的青春身影?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一个人到处转转,找村民聊聊天,问问当地是否有留存的古迹。岱头可有奇岩?可有特别的景致?有。在哪里?且随我去看看。
从东头村委会沿着公路往西走,到了岱头停靠站前方,沿着一条长长的台阶往下到了仰口坦老屋,然后顺着西侧的鹅卵石路约行20米就到了驮岭。五格蒸笼岩就在路坎下。

驮岭北侧为山坡,南侧是竹林。竿竿翠竹傲立着,直插云天。那密密的竹叶遮住了阳光,零零碎碎的光从叶与叶的空隙里透出来,形成一小块一小块光斑。一阵风吹来,竹影婆娑,荡绿滴翠,煞是好看。如今正是竹子冒尖的时候,几根竹笋拱出地面,好奇地看着我,勾起我强烈的食欲。

这里的地面皆为裸土,竹子长在泥土上,竹叶落在泥土里,一切都是安然宁静的。我走到一处坎下,赫然发现有岩五个叠起如塔状,又如蒸笼状,故名五格蒸笼岩。据《文成乡土志》记载:五岩重叠高3米,顶岩高1.5米。岩面覆有青苔。这些石头有多重?无法估算。附近都没有大石头,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它们待在这里多久了?几百年?几千年?抑或几亿年?难道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海洋?谁能给出答案?“五百年桑田沧海,顽石也长满青苔。”我想,这些石头站在这里的时间绝对不止五百年。

因为最上方的石头能摇动,因此也叫摇动岩。这么重的石头,怎么能摇动?我表示怀疑。村民上前,双手攀住顶岩,脚踩在第四块石头上,“腾”的一下站在顶岩上,慢慢移动双脚到了岩的北侧,左右摇摆,岩石真的动了。太神奇了。

除了摇动岩和五格蒸笼岩这两个名称,有人还称之为“岱王印”。这是怎么回事呢?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家住岱头的岱头王是神仙的舅舅。神仙每年正月初二都来岱头“貌舅舅”(“貌舅舅”就是来舅舅家拜年,玉壶人称拜年为“貌节”)。一次,神仙挑着担子又来岱头“貌节”了。那天下着雨,雾气浓厚。神仙的担子一头是泥土,一头是五格蒸笼,蒸笼里装着五块大石头。走着走着,到了九龙和驮岭之间。雨慢慢的变大,瓢泼似的直往地上灌,路上也没有躲雨的地方,担子里的泥土经雨水的浸泡越发沉重了。神仙举步维艰。

神仙正在懊恼之际,前面走来两个小尼姑,合撑着一把伞,一边走,一边嬉闹着。“喂,两位小姑娘,这是啥地方呀?我要去岱头,还有多少路呀?”神仙问道。小尼姑停了下来,好奇地打量着神仙:一个大男人,浑身上下都是雨水,担子里有泥也有石头。小尼姑想逗逗神仙,就说:“岱头呀,远得很哪,喏,在对面那座山后面的高山顶上。下这么大的雨,您还是歇歇再走吧。”此时神仙的担子一头在九龙,一头在驮岭,只要再跨一步就能到达岱头。神仙根本就没想到尼姑会逗他,还信以为真,于是停下担子,心想:等雨过了再走吧。
歇息了一会儿。终于,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神仙俯下身子准备挑起担子继续赶路,没想到担子却挑不起来了。无论神仙如何用力,那担子就像长在地上似的一动也不动。为何会这样?这些石头和泥土原本住在天上,一旦沾上地气就会与土地连在一起。神仙没办法,把箩筐里的泥土一倒,泥土就倾倒在九龙的山坡和稻田里。如今你去九龙看看,那里土肥地沃,稻子粒粒饱满,年年丰收;山坡树木成林,枝繁叶茂,据说就是因为那里的泥土是神仙挑来的缘故。神仙又把蒸笼一抽,那五块岩石就稳稳地静卧在驮岭坎下,这就是五格蒸笼岩。
神仙给岱头王“貌节”的礼物为何是泥土和石头呢?原来,这也是出于一份好意。你想呀,在那农耕时代,地肥好种吃呀。把这么肥沃的泥土送到岱头,岱头人种田不是能增收吗?那五块石头就是岱王印,以后岱头王起义成功了,这就是玉玺呀。
传说归传说,现实还是现实。看着五格蒸笼岩,我不禁想,是谁让它来到这里的?在来到这里之前,它有过怎样的经历?它是否曾站在高高的山上历经千百年的时光流转?是否目睹了无数往事,收集了无数故事?如果我用心去倾听,它会告诉我它所经历的那些严寒酷暑,那些风雨,那些地动山摇吗?如今的它犹如一位睿智的长者,经历过那么多的壮观和震撼却心如止水,岿然不动坚硬如铁地站在这里,只看熹微的晨曦,只看漫天的晚霞,直到月光西斜,直到夜露深重。
岱头有一条山岭,人只要站在岭上,便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芳香气味。这话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去看看吧。

从东头村委会出发,过株垄,沿着后畔山的屋基塆往东走,前方是由块石铺成的山岭,此即香岭。岭北侧有数间砖木结构的两层落地房,这是东头卫生所旧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颇为热闹,村民有感冒发烧的都来这里看看。后来随着城镇化和集约化发展,岱头非流动人口减少,医生调走了,房子也空置着。古时候,玉壶前往汤垟、朱雅、吴坑、大南垟、坳头、双坑、黄河、南山头等地必经香岭。因为这是唯一的通道,来往的行人尤其多。粜火炭的、扯兔子毛的、砍柴的、狗踏碓的、唱长筒的、唱元宝的、走亲访友的、接送新娘子的、上学的,路上行人可谓是络绎不绝。

继续往上,岭的北侧是稻田和菜地。稻子已经收割,尚未耕种,稻茬安静地站立着,接受雨点的洗礼。菜地里的马铃薯和生菜茂盛地生长着,绿得透彻,绿得纯粹,绿得肆意,植物的清香远远近近地逼来。岭的南侧是山坎,长着各种杂草,金樱子、大竹叶、毛刺草等笑得欢畅而随意,它们想长哪里就长哪里,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想长多高就长多高,此地空旷也没人管呀。其上是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松树、枫树、杉树都有。在山岭之间,在树木之间,在庄稼之间,时光在这里潜藏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只等你我来挖掘。

20世纪70年代之前,农村经济落后,烧火烧土灰盖房子做家具处处都用到树木和杂草,岱头本地的山上光秃秃的,连草都难得见到几根。后来,村里为保护杂草树木下令封山,任何人都不得上山砍柴割草。可要烧火做饭怎么办?村民只能带着草刀,拿着冲担去园丰林场和三亩等地去砍柴。于是,晴天的早上,经常能看到一群一群的男人步履匆匆地走上香岭。这时,一阵阵芳香扑鼻而来,浓烈馥郁,丝丝缕缕,浮荡在雾气中。越往上走,香气越浓。山上气温低,但弥漫的香气却能让人久久地沉醉其中。约行100米,芳香渐渐消失。复前行,香气全然消失。
更令人奇怪的是:香气随季节而变化,冬天浓,夏季淡,一天之中清晨尤甚。香岭之香从何而来?村民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前,香岭南侧约500米的地方有一片名为龙头的山林,长满羊乳草,香气是羊乳草散发出来的。羊乳草为何会散发清香?请听我慢慢道来。

玉壶人称羊乳草为奶奶草。我用手机“形色”来识别羊乳草,得知其书名为四叶参,桔梗科,多年生缠绕草本,长达2米以上,折之,有白色乳汁,如羊乳,故名。其根呈纺锤形或类圆柱形,粗糙不平。每到三四月份,芥菜成熟之际,岱头人喜欢挖来羊乳草之根,加上柚子皮、笋和芥菜梗熬制粘菜糖(也称为菜梗糖)。
龙头在哪里?那里还有香气吗?我跟随村民来到株垄,沿着南侧一条小路往山上走,约行200米,来到一块大田里。村民告诉我,岱头西侧的山脉形似一条龙,故称龙脉,龙头就在这块大田的后山上。稻田后方为山坡,百草丰茂,树木丛生,间或有几株羊乳草,数量不多。我折断一根羊乳草仔仔细细地观察,断折处有白色乳汁溢出,其藤为粉色,嫩嫩的,四叶攒生一处。细闻,有一丝淡淡的清香,应该是青草的气息。我面对后山站立着,可未闻到有香味袭来。
也有村民告诉我:香岭的香味并不是羊乳草散发出来的。当年村民也曾在香岭附近查找香气的来源,但找遍山上的花草树木,皆无此香。有的人觉得是某种微量元素由岩层中释放开来在空气中所形成的,是耶否耶,谁能考证?谁能说得清?香岭的香气到底来自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个谜。
后来,龙头的羊乳草慢慢减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香岭上的香气渐渐淡了,后来就消失了。

拉长时间的轴距。20世纪90年代初,岱头人生活普遍好转,有人开始琢磨该让香岭改改面貌,这样也好走一些。于是,胡从路、胡克献、胡克令和胡克光等人首事,筹集资金,买来条石铺设香岭,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纷纷前来帮忙。不久,香岭面目一新成了如今的样子。
这时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回到香岭。在这样的山坳里,在这样的山岭上,我无处躲避,只好拾级而上,四处唯有寂静,唯有雨声,唯有鸟鸣。我用力呼吸,可依然没有闻到一丁点的香气。
那丝丝缕缕留存在岱头人记忆中的香气终究被时间带走了,且不留一点痕迹,甚是遗憾。而这石板路也才30多岁,虽然其身上还留有古道的痕迹,但外表还是稍显年轻。我的双脚轻轻叩在石板路上,静静听它平淡平和地述说着曾经的过往,没有一丝叹息。几位上山下山的村民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身影与身影擦肩而过。那些曾经的故事,那些曾经的香气都已经绣进青石板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片树叶都镌刻时光的痕迹,记载着历史的风云。
在吕溪和东头一带,你时常能听到老百姓聊起这样一句话:岱头出王,茗垟出将,溪源出军师,吴坑出娘娘。在《茗垟》和《溪源》这两篇文章中,我已经写过周大将和徐军师的有关传说,这里就不赘言。“岱头出王”,这“王”指的是谁?
据《故诚意伯刘公行状》记载:初,公言于帝,瓯括间有隙地,曰谈垟,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顽民负贩私盐,因挟方寇以致乱,累年民受其害,遗俗犹未革,宜设巡检司守之。帝从之。及设司,顽民以其地系私产,且属温州界,抗拒不服。适茗垟逃军周广三反,温处旧吏持府县事,匿不以闻,公令长子琏赴京奏其事,迳诣帝前而不先白中书省。时胡惟庸为左丞,掌省事,因挟旧忿欲构陷公,乃使刑部尚书吴云訹老吏讦公,乃谋以公欲求谈洋地为墓地,民弗与,则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几可动帝听,遂为成案以奏。翻开《名山藏》,也得到如下记载:章溢既至,召所部义兵令元帅兴率以讨贼,贼皆败,复遣存道斩叛贼遂卿于茗垟,收集其故部,曲得乡兵二万送京师,太祖大悦。
根据上述材料,“岱头王造反”是真实的。但因为年代久远,民众只是口口相传,难免会增加一些神话的色彩,以致民间传说与史书记载有出入。岱头王是谁?据史料记载,周广三和周遂卿是茗垟人,他们是不是岱头王?抑或另有其人?岱头王为什么造反?何时造反?村民缓缓讲述,我用笨拙之笔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岱头王形象。

传说元末明初时期,岱头有个农民生得虎背熊腰,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力大如牛,能举500斤石臼,且性格耿介刚直,善良公正,不阿权贵,好打抱不平,时人称之为岱头王。岱头王喜欢骑着一匹白马从岱头出发往西至溪源,往南到茗垟,“哒哒哒”的马蹄声踏响了悠长的古道。岱头王带着一帮兄弟贩卖私盐,地点就在“瓯括间之隙地”——谈垟。为什么选择谈垟呢?这与谈垟的地理位置有关。谈垟在明清时期属嘉屿乡(属瑞安县管辖),此地北边是青田地界。既为“隙地”,瑞安和青田两县都难以管辖,由此,盐贩、盗贼等常聚居此地。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县贩卖木头的地点在瑞安寨下和文成桂山,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两县交界处,瑞安和文成都无可奈何。其次,与芝溪有关。芝溪发源于南田镇十源乡叶山头村,过十源、金星、北坑、碧坑、溪源、玉壶、林坑口、寨下,在营前注入飞云江。古时候没有公路,买卖私盐一是肩挑背扛,二是靠竹排运送。岱头王伙同兄弟们从宁波、温州等地通过竹排将私盐运到谈垟出售,因为运费低、价格实惠公道,谈垟、二源、十源,甚至黄坦、西坑、玉壶一带的村民都喜欢购买岱头王的食盐。从营前到谈垟,竹排一路前行到了有村庄的地方,就有人过来买私盐。如玉壶外楼门前溪埠头、垟头、溪源等地,村民也与岱头王以及一帮兄弟熟悉了,竹排到了,吆喝一声,就会有人来接应。

我们再来说盐业政策。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提出“盐铁官营”。历朝历代的盐业铁业政策虽然都有变化,但将盐和铁掌控在官府手中的中心思想始终不变。与官盐相对的就是私盐,这是暴利行业呀。数点历史上那些造反之人,比如黄巢“本以贩盐为事”,程咬金是私盐贩子,张士诚是“盐徒”。私盐贩子为何爱造反?人家胆子大,腰包肥,有资本呀。久而久之,岱头王生意越做越大,随之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可谓是赚得钵满盆满。有了钱,他们的胆子也更大,贩卖私盐也更猖狂了。谈垟俨然成了一个四方货物的集散地。我们再来说贩盐的后果。古时候,因为盐的税收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之一,官方严控食盐买卖。食盐只能官卖,而且规定:只能购买当地的食盐,不能私贩。贩卖私盐,历朝历代都将之定为重罪。如《大名律》记载:贩卖私盐,杖一百,徒三年。若携带兵器贩卖者,罪加一等;拒捕者,斩。
官方不让卖,岱头王偏要卖。为此,岱头王跟官方闹,也是所谓的造反。造反可不是随意说说就能成功的,需要有人谋划,有人领兵,这就需要军师和大将。听闻茗垟有一位力大无穷的周姓农民,岱头王亲自去拜访,周姓农民以母老患病不便远游为借口婉言推辞。后周母病逝,岱头王暗中相助,周姓农民感动前往岱头拜谢,岱头王便封其为统兵大将。得知溪源水源头一徐姓少年有呼风唤雨、除妖捉怪、剪纸为马、撒豆为兵的本领,岱头王封其为军师。岱头王又暗中招兵买马备盔甲,在朱寮铁炉坦炼铁造兵器,将军队驻扎在茗垟寨山。
有人将此事上报官府,经查实,浙江行省命镇守在处州的章溢领兵前往茗垟围剿岱头王。头一个回合,岱头王率领士兵下山厮杀,将骁兵勇,官兵大败。
却说明军中有人懂堪舆学,谓岱头村前有岩五个,那是岱王印。如能破除,岱头王必败。章溢命人扮成商贩混入岱头村,以重金买通石匠凿开“岱王印”,灌入白狗血。随后,明军兵分三路突然袭击,将岱头和茗垟层层包围。徐军师获报,仓促之间准备不及,把剪好的纸兵和做好的豆兵放出来迎战。豆兵因为尚未点睛,只会横冲直撞,对着岱头王的兵士用力冲杀。官兵掩杀而来,徐军师知道大势已去,仰天长叹三声,只身逃出茗垟,直奔溪源军师坑边上的水源头岩头下,藏匿其中,不久忧愤而死。

我们再来说周大将。听闻禀报,周大将大惊,急使人告知岱头王,自己则披挂上阵,率兵迎敌。此时,明军已漫山遍野包围过来,喊杀声响彻四面八方。周大将骁勇对抗,砍杀十多名官兵,但无奈势单力薄,被围垓心,虽左冲右撞仍无法脱身,终因寡不敌众,与士兵一起力战而死。
至于岱头王,彼时正是酒醉初醒,突闻敌军来袭,急忙上马挺枪率领士兵一起迎战,一时势不可挡,官兵被杀得节节败退。可时间久了,官府的援兵到来,官兵越战越勇。激战多时,岱头王的士兵纷纷被杀,越战越少,最后只剩岱头王一人单枪匹马而战。官兵从四面八方层层包围。明军下令弓弩手万箭齐发,岱头王不敌,人马俱伤,马跌人倒,被当场擒斩。
就这样,岱头王连同他的故事,他的传奇,他的风雨人生,在茗垟寨山成为终局。

坐在岱头印的巨石前,听着村民缓缓讲述岱头王的故事,感受点点细雨落在发间,落在肩膀上那凉凉的感觉,忽然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感,不知是自己走进了历史,还是历史来到了现实;不知是自己走进了传奇,还是传奇来到了身边。
夜色缓缓地笼了过来。我再回头看一眼岱王印,终于决定离开,山路蜿蜒,渐行渐远,回望那一片竹林,却只见竹林边上的老屋挺立着,岱王印已经模糊了。夜幕笼罩,五格蒸笼岩也已经被湮没。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扛着一辆自行车跟着同学从岱下岭出发,过岱下直至岱头,只为了要去黄河摘几个梨子解馋。那时玉壶至东头的公路尚未通车,路面坑坑洼洼,我们到了岱根,有人提议:骑车去岱头费力,不如扛自行车走山岭。年少懵懂的我们竟然照做。

从那以后,我忘了有多少次,只要一想到岱头,就有来自岱下的风声从记忆中穿过。流光一瞬,美好一身。岱头的茅草屋,青石墙,风中雨,林间鸟,还有那静静的山野,都成为时光中的每一寸柔软,成为我记忆中的永远。
如今再一次走上岱头岭,只见半春繁花盛开,半路枝叶葳蕤,而我已然半生岁月饮尽。在满目的翠绿中,我深深地呼吸着,吐纳,轻轻地招手,犹如故人归。不知岱头岭是否还记得我儿时的样子?是否还记得我清脆响亮的笑声?是否还记得我肩扛自行车的身影?没有谁能重复昨天的故事,不变的只有往事浮沉,风声依旧。
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几代人口口相传的美丽传说,在岱头这片土地上,每一滴露水,每一阵清风,每一根草木都渗透着浓浓的乡土情怀。
上一篇: 量价齐跌倒逼沙洋苗木工业转型
下一篇: 杜恩湖对话刘双平:赵本山背面的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