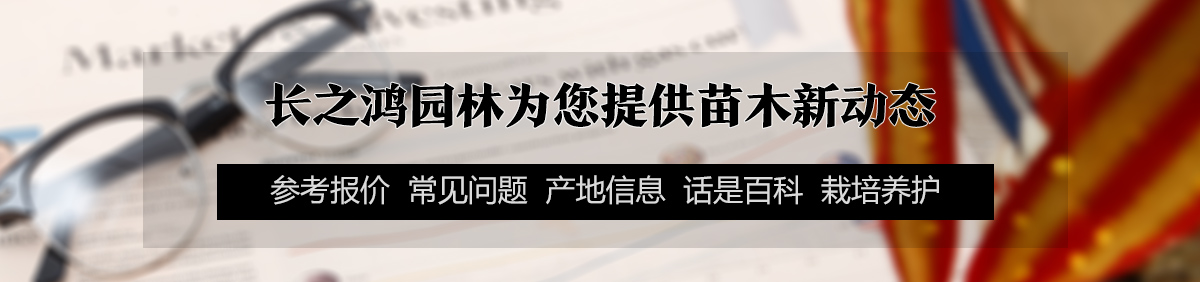在1976年(丁晓平)
1976年10月6日,逝世后的第27天,“”终于被打倒了。“”一倒台,的复出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10月8日,当选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依然坚持生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种局面和形势下,由授意建立起来的国务院政研室,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台上的时候,受到“”的打压,外部受气;“”垮台了,内部出气了,但外部依然在受气。而作为政研室的主要负责人,更是里外受气。
——逝世后,中央组织机关单位的负责人都去守灵,却唯独政研室没有资格。后来,政研室的少数负责人分批去了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唯独没有资格。
这对来说,是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邓力群就劝说:“你写封信吧。”无奈之中,就给和写了一封信,请求见最后一面。可想而知,不可能答应这个帮和她唱“对台戏”的的。
——的追悼大会是在9月18日召开的。中央通知每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登上城楼临时搭的观礼台。国务院政研室就推荐了和邓力群。
谁知,名单报上去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突然打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别上台了。”和邓力群没有很好的方法,只好吞声忍气。
1976年10月18日,中央发出了十六号文件《中央关于王洪文、、、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先后五次组织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了讨论学习。10月20日、21日、23日,一连三天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了北京市的。
10月27日、28日、29日、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又接连召开了五次揭批“”的会议。但就在“揭批”会议上,再次成为政研室内部的揭批对象,会议充满着火药味。这对的精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原因就出在给写的所谓“效忠信”上。这封信在逝世后,竟然把它公开印发出来,这一下子给的打击更大。
出于敬仰,像这样长期在身边工作且深受毛喜爱的人,希望能参加毛的遗体告别仪式,见毛最后一面,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竟然禁止参与任何与追悼有关的活动,这确实令伤心。无奈中他给写了信。
但是不是“效忠信”呢?说:“我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并转,其中有一句话:对于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虽然不能仅仅因为这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明的信是所谓的“效忠信”,但的这些话,在“”倒台后,确实令许多看到这封“效忠信”的人感到意外和气愤。
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写这封信的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信的原因是“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公开批判他,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为了能见上最后一面,既委屈,又悲伤,为了“报答毛主席”,抱着这个单纯意念的他万不得已给写了这封信,说了违心的话。
而就在国务院办公厅宣布解散政研室的这次会议上,尽管没有参加,但还是有人提出了批评。有人说:“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啰而已。”话确实太尖锐了。
还有人说:“在粉碎‘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十分清楚政研室内部矛盾关系的邓力群,会上跟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说:“谁都知道嘛,受‘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我们每个人不都批判过他?!还有批判更厉害的,李鑫同志不就说过人家‘不是个玩意儿,我总算看透你了嘛。同志确有错误,但怎么能与‘的小帮派连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其实,这样一个时间段,他们或许都还没想到,解散政研室并不仅仅因为是要打击,更是冲着来的,其目的是要剪去的“羽翼”,使即使复出后身边也没有“笔杆子”,组建不起来理论队伍。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鑫主持起草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每天坚持看报纸的指着《人民日报》对家人说:“看来邓的复出恐怕又困难了。”
1977年3月,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共同向主持会议的提出要求重新出来工作和“”。已经多次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对自己从来就是自信的。
“”倒台后,他清楚自己的复出已经指日可待。在听到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之后,他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我们一定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央转发了的信。
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复出的问题已摆到了主持的高层工作会议的桌面上了。而1976年3月2日写的“揭批”的材料,一石击起千层浪。当时,高层的、王震、、陈锡联、罗瑞卿、等对非常不满意。
有的说“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不能原谅”;有的说“顶不住啊”;有的说“怎么能这样干”,等等。就连陈云、这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也很不高兴,颇有微词。
其实,写揭批的材料时,确实既矛盾又痛苦,前前后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而且一直都是瞒着家人写的,连夫人谷羽都不知道。直到“”印发后,家人才看见,都责怨他不该这么写。家里家外,议论纷纷,确实感到十分窝火,更觉得难过和委屈。
好在邓力群等人坚持为说真话道实情,并得到了陈云、王震等老人的理解。
王震和邓力群等人知道,复出后,“笔杆子”非莫属。当他们了解愿意与政研室留守人员见面的消息后,就马上建议给写封信,作自我批评。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和邓力群就带着的检讨信来到了的家中。
一见面,邓力群就跟说:“小平同志,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
邓力群连忙解释说:“乔木在事实的揭发上没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就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
笑着说:“这没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材料我看了。没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这样讲,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你告诉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针对政研室李鑫等人批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的问题,却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知人善任,这就是的高明之处。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再三叮嘱邓力群,说:“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